李娟的散文以及改编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,让阿勒泰成为很多人向往的远方。阿勒泰也成为文学版图上一个重要的存在。近日,花城出版社“西遇记”系列推出散文集《克兰河畔》,该书作者巴燕·塔斯肯是一名出生于1999年的哈萨克族青年作家。巴燕在阿勒泰度过童年。成年后离开家乡前往广州求学,如今毕业回到乌鲁木齐定居。在《克兰河畔》中,巴燕以质朴澄澈的语言讲述阿勒泰的母亲河克兰河畔发生的故事,写出一个本地青年对故乡、根脉以及土地的心灵归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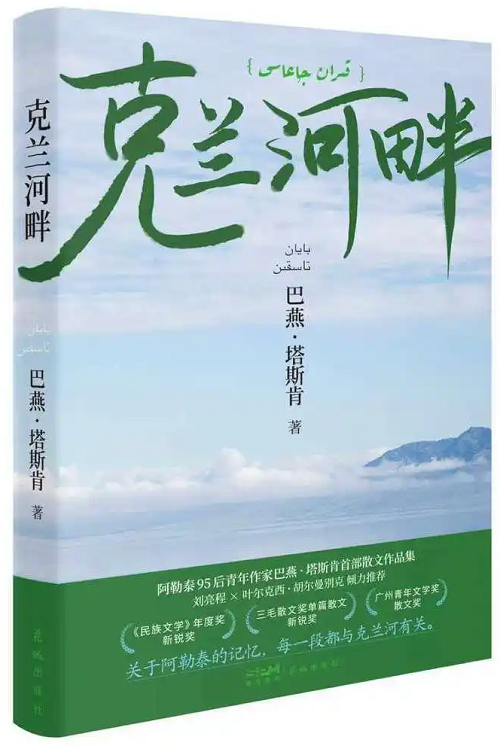
《克兰河畔》
刘亮程点赞:
有阿勒泰的气息,是那里生长出来的文字
“克兰河畔的春天是慢慢来的,是突然发现的,是悄悄走的,是永远怀念的。”克兰河畔的童年时光,成为了巴燕永恒的记忆。在《克兰河畔》中,巴燕以哈萨克族少年“我”的视角,讲述了阿勒泰克兰河畔的乡居日常。书中通过“地里的庄稼、圈里的牛羊、屋后的白桦林”等质朴意象,勾勒出村庄四季流转的生活画卷。从上游到下游,巴燕的家族曾游牧于阿勒泰群山深处,后定居于克兰河畔。他说:“我们几代人的生命好像全用来丈量一条河。”这本书,正是对那条河、那片土地、那一段从游牧到定居的民族记忆的深情回望。
在沿河而生的白桦林间,少年巴燕跟着爷爷年复一年拾走漂流而来的玻璃瓶。邻居家走失的花白奶牛,靠放牧时口耳相传送归原主;外地慕名而来的汉族画家,驱赶走河里电鱼的人,成了当地哈萨克族儿童争相效仿的英雄;“哈萨克一半的财产都是客人的”等传统礼节融合于叙述之中;最后作者南下求学,往返于内地大城市与阿勒泰的经历。少年在接受与不舍之间、在自然与现代之间思考,真实还原了一个哈萨克族青年眼中的世事变迁。著名作家刘亮程推荐这本书时说,“巴燕的散文有阿勒泰遥远牧场的气息,是那个地方生长出来的文字。”《克兰河畔》同名散文曾荣获“三毛散文奖·单篇散文新锐奖”。
【对话巴燕】
“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带着家乡的一阵风”
10月29日,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巴燕,听他讲述自己开始写作故乡的缘起与作品背后的成长故事。
封面新闻:这本散文集被视为您对阿勒泰的深情回望。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动笔写自己的家乡?
巴燕:这本散文集中写到的故事都发生在阿勒泰市旁的小村庄。我很小就被父母送到了祖父母身边,从我记事起我就在陪伴着两个老人,每天的生活就是跟着大人去放牧、种地,直到我长到有力气能拿起一把铁锹,能独自走完去放牧的路。我也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在村里劳作的人。那段时间我非常想念在城里打工的父母,当我离开祖父母身边去城里上学时,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村庄。我每次去看望祖父母时,好像童年那种孤独的、寂寞的情绪一直在等着我,随时准备将我淹没。这样过了几年,我就南下去广州求学去了。当我走在广州的街头,那个城市的建筑、街道、路人,哪怕是一棵树一棵草都是我没见过的品种。尤其是岭南地区特有的文化,是我以前从未了解过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浓烈的思乡情绪促使了我提笔写作。我起初是想写出童年的那种寂寞的生活,还有遥远的家乡。没想到,当我再次回忆那些不愿想起的往事时,才发现我已经原谅了许多人和事。所以只有那些轻松的、愉快的,充满了童趣的经历被我写了下来。作为一个新人写作者,它见证了我的成长。同时它也是一本装有故乡万物的载体,陪伴着我离乡的每一个日夜。
封面新闻:这种地理上的穿梭让您对“故乡”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改变?
巴燕:刘亮程老师曾说过:“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自己的故乡”。我经常会提到这句话,因为我觉得自己当下就是这样的状态。我觉得每一片土地都是有性格的,它孕育出来的人,也是如此。我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上带着家乡的一阵风,这种东西是很自然的。我在城市里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人,但很少,他们的每句话里,眼神里,都藏着他们故乡的特质。
封面新闻:接下来,你还会继续写阿勒泰,还是会将笔触转向你正在经历的、更为复杂的都市生活与文化碰撞?
巴燕:我已在继续书写下一本书,也是一本散文集,顺利的话预计明年出版。不同的是,我不再专注于故事的本身,而是着重于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感悟娓娓道来。《克兰河畔》出版后,花城出版社在阿勒泰为我举办了新书发布会。我回家探望祖母时得知,村里又有好几位老人离世了。我也在书中写到过他们。当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离去,年轻人也在外求学、追梦。只剩那么几个年轻人在村庄,开农家乐、做旅游。然后我就设想,如果当初我也没有离开村庄,而是继续在村里生活、长大,走到娶妻生子,走到生老病死。那时的我,会想一些什么?于是,我就不再执着于非虚构写作,而是将自己重新送回那年的夏天。我站在桥头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去追梦,等所有人离去后,我转身向土地里走去。我捡起昨天扔在地头的铁锹,找回丢失的牛羊。这个村庄不能再有人走出去了。这些是我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想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封面新闻:你这本书读起来有一种清澈的童真气质。这是你特意为之的吗?
巴燕:说特意为之也不为过。它本来就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讲的故事。那些过于深沉的、复杂的气质,与一个活泼的新生命不符。
看李娟笔下的阿勒泰感到“很亲切”
封面新闻:你的语言被评价为“质朴清澈”、“灵动跳跃”,同时又带有哈萨克族口头文学的韵味。你如何形成这种独特语感?
巴燕:这本书中我融合了一些民歌、谚语、习俗。文字质朴是由于我的汉语词汇量太少,文化水平有限。比起用一些陌生的字词,我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、简单的字词来叙事。因为在我看来,写作最重要的还是真诚。在能力范围内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书写,一定不会太差。
封面新闻:提到阿勒泰,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李娟。她的《我的阿勒泰》等作品很大程度影响了许多远方读者对那片土地的想象。作为阿勒泰本地人,你如何看待李娟笔下的阿勒泰?
巴燕:我读过李娟老师的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《我的阿勒泰》,感觉非常亲切。虽然我本身不是一个在草原生活过的人,我也没经历过那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,但是从她的文字里我看到了遥远的祖先的生活。从父亲的少年时期开始,我们就已经在山脚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。所以我对草原是陌生的,我是一个在村里长大的人。《克兰河畔》这本书里也几乎没有关于草原的生活,即使有,也是去做客的经历。所以我很喜欢看李娟老师笔下的草原故事。
来源:封面新闻 | 张杰 朱萌丽
